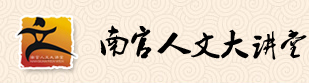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访杭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曹布拉教授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庄向娟 发布时间:2007年04月20日
曹布拉教授祖籍黄岩,却出生在杭州,小时候有一段在路桥的经历。这次将到路桥,在南官人文大讲堂上讲第二讲——曹不拉眼中的金庸。日前,记者约访了他。记者:你怎么会喜欢上武侠这种虚幻的文学作品的?第一次接触金庸作品时,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曹布拉:人总是对自己陌生的事物怀有好奇心。我从前爱读美国昌德勒的“硬汉派”侦探小说,觉得它们不仅情节吸引人,对话机智,还塑造了丰满的人物性格,有较强的文学性。初读金庸的时候,折服于其丰富的想像力——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比较缺乏的、丰厚的意蕴、鲜活的人物及雅洁的语言;以为他是打通了雅俗,融汇了中西,把侠义小说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记者:金庸的作品几乎部部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像《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等。但大陆近期拍摄的金庸武侠电视剧却饱受批评,您认为这里面的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曹布拉:我不以为大陆的金庸剧有多糟糕。一般来说,把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本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一旦改编成影视,便兑入了制片人、导演、演员们的二度创作,有了这些人的风格及审美取向。大陆金庸剧在画面的美轮美奂、特技的娴熟运用和演员的青春靓丽方面还是不错的,很具视觉冲击力,让观众得到感官的享受。如果说有什么欠缺,主要是导演在使用演员时过多考虑演员在当时的票房号召力。
记者:金庸小说中,大多是一些抑强扶弱、行侠仗义的侠士,您认为这样的精神对于现代社会是利多还是弊多?
曹布拉:现代社会是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以武犯禁”的古代侠士当然没有容身之地。但中国文学作品中“侠”的人格精神,如果是指那种具有深广的同情心、为利益大众而奋不顾身、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一往无前、当灾难降临时独力担当的大无畏气概、对高洁理想的坚守的人格精神的话,即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超迈的大丈夫人格,那么我觉得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还是有益的。
记者:记得《藏龙卧虎》在英国上映时,由于不能理解现实和虚幻同时存在的武侠文化,看到现实历史背景中的人物突然飞上了屋顶,全场轰然大笑。这对中国的武侠文化或许是一种悲哀?
曹布拉:美国的《超人》、《蜘蛛侠》中的主角的飞行能力似乎更胜一筹,但不知英国观众看了是否也哄堂大笑?记得一位搞影视的朋友曾说:好莱坞电影如“007”系列,整个故事肯定是假的,但导演硬是往细节上下功夫,把它弄得很逼真,使观众有身临其景的真实感;而许多国产片故事是真的,但导演偏偏要把细节弄得很假、很做作。这样的影片,我想不单是英国绅士,我们看了也会发笑。
记者:你个人偏爱金庸作品中的哪个人物?
曹布拉:萧峰,他是金庸笔下第一号男子汉大丈夫,喜欢的理由即在于此。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学术这条道路的,您能给路桥的学子们说些什么吗?
曹布拉:我虽出生在杭州,但父母都是黄岩人,舅舅就在路桥。我小时候曾在外婆家住过一阵,还读了半个学期的一年级,是在田际小学。我初中毕业时去了黑龙江插队,回到杭州后做过临时和正式的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时上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文化、教育单位辗转谋生。写过一些小说,也出版过几部武侠小说。2000年到大学里谋得一只饭碗。大学里是讲究“学术”的,我不会学术又不愿下岗,只好强迫自己学着做“学术”,炮制一些能在大学这个环境里勉强得到承认的文字。但我心里很明白,本人没有一点学问底子,这辈子也不可能成为“学人”,最多只能算个杂七杂八的“杂学”人,很难为家乡的年轻朋友贡献什么有益的意见。我在学校里,有时兴之所至,也会给学生们讲几句倚老卖老的话。我说,对年轻人来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多读点书,应该不算坏事。中国人是讲实用的,读书可以多长知识,学会本领,古人曾以“颜如玉”和“黄金屋”来利诱人们去读书。但读书的用处并不仅在于此,我以为,多读书可以多长见识,多明白些事理,帮助人们弄清楚:人活着为什么?什么才是幸福?今天的大学里,也有学生家境很好,花钱如流水,我偶尔问他们,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很幸福吗?他们中很少有人作出肯定的回答。他们也有他们的精神痛苦,那就是不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知自己爱好什么,对什么有浓厚的兴趣,感到迷茫,找不着北。我完全能够理解,没有找到精神座标的人即使再有钱,也是不幸的人。所以,我是主张年轻人为寻找自我、寻找人生意义去读书的——当然,我也知道这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境界,我自己就做不到,哪有资格在这里开导别人呢?我们只能“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