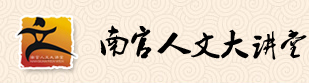让我们迎接独立而健美的知识女神
——访中国红学会会员、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乘健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庄向娟 应佩娜 发布时间:2007年06月01日
记者:《红楼梦》里面,除了贾宝玉这一男性以外,林黛玉、王熙凤、贾母这些女性形象鲜活,是文中的主角;而在《水浒传》中,女性多属配角,命运颇为曲折,甚至丧命于刀剑下。两者的不同,是否真的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妇女态度的变化?在同一时代,为何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妇女观?张乘健:《红楼梦》与《水浒传》观念的迥然不同的原因,一是时代的演进。《红楼梦》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正是欧洲社会革命和文化革新风起云涌的时代,是出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时代。《红楼梦》的作者虽然与当时的西方文化似无直接交流,但似乎和当时的西方先进思潮遥相呼应。《红楼梦》中出现一个异样的“真真国女子”,居然是一位金发碧眼女郎;《水浒传》则酝酿写成于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其时中国与西方一样,虽然看起来社会现象上很繁荣,但实质上仍处于“中世纪的黑夜”。二是作者经历和观念的差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经历大起大落,身心创痛,从而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反省和批判;而《水浒传》作者——托名于“施耐庵”,至今未能考定究竟是谁——看起来愤世嫉俗,其实骨子里思想却很正统,整部《水浒传》贯穿着的似是“奸臣祸国论”,与“奸臣祸国论”相互表里的竟然是“女人祸世论”,尤其是“美女祸世论”,更可悲的是,“美女祸世论”,竟然与“淫妇祸世论”成了同义词。
记者:就妇女观而言,《红楼梦》里所反映出来的妇女观是本土的产物,这和西方的传统又有何不同?你认为我们当今就妇女观问题应该向西方学习些什么?
张乘健:这个问题提得对极了。《红楼梦》看起来与《水浒传》反其道而行之,《水浒传》是“男贵女贱”,《红楼梦》则是“男浊女清”。贾宝玉看起来对女子很尊重很爱护,实际上仍是中国式的贾宝玉式的的“怜香惜玉”,甚至是“倚红偎翠”。贾宝玉后来对这种“怜香惜玉”、“倚红偎翠”深自忏悔,正是这种“怜香惜玉”、“倚红偎翠”把金钏等青春女子害死了。西方的所谓“女士优先”,直译应是“女士第一”(lady first),所表现的是男人有教养的标志,表现的是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古希腊文化体现一种优美壮美的女神崇拜,这不仅仅是形象,而是一种精神意义。在中国,是女神的失落和女神的变形,《红楼梦》开篇的第一个人物是女娲,女娲炼石补天,多么壮伟有力,但女娲隐形了;《水浒传》中,梁山首领宋江真正受启示是神秘的九天玄女,这个九天玄女似乎像阴谋的道姑。中国的法律象征是吓人的黑面包公,古希腊的法律女神竟是一位半裸体的妩媚的清丽女子,这在中国,简直不敢想象。受西方精华文化的启示,呼唤和再造中国的壮美的女神。
记者:但西方的妇女观并没有直接催生出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而是通过牺牲和几代人的奋斗,才获得了应有的权益。我国已经在法律上明确了妇女的地位,而在实际中,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仍处于从属的位置,对此你怎么看?你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宣传新妇女观能在多少程度上被接受?
张乘健:任何纸面上有价值的文字都是血写的,西方的男女平等的法律是近代革命的结晶,也是数千年历史演进的结果。在古代欧洲,不仅男、女不能平等,男、男也没有平等。即使在现代的西方,真正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仍然是文学作品中的浪漫的理想。古代罗马的“罗马法”(Civil law),看起来很文明,实际上是通行于贵族之间的法律,根本不普及于平民,更谈不上奴隶。近代革命,将“罗马法”下移,称之为“民法”。我们现在颁布的“民法”,明确了妇女的地位,明确地表明男女平等,明确地表明女子与男人一样有同等的名誉权、命名权、工作权、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这非常地来之不易。但是,从纸面到实际,仍须付出艰巨的努力。妇女未能真正地自立,在我看来,农村、城市都一样,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古代中国有“叶公好龙”的故事,近代中国人是“叶公好凤”,有些人口头上高唱妇女解放,但真的解放了的妇女站在他面前,他受不了了。正是因为新的妇女观在相当程度上未被接受,所以要大声呼吁,你越是不大愿意听我越是要讲。都接受了还讲什么?你请我吃茶好了。
记者:新的妇女观有时候是和西方性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宣扬妇女应该更为主动地追求婚姻、家庭甚至是性爱的幸福,而不是始终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但在我国,一提起这样的事情,往往会遭到舆论的群起而攻之,你认为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
张乘健:这个问题太复杂也很微妙了,和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哲学甚至和生理学、心理学都有关系。所谓“性解放”,是很容易引起歧义与误解的。以我的理解,所谓性解放,实际上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制度的检讨和反抗,实际上是提倡人性的解放。在人类远古社会,长时期处于无所谓家庭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社会的建立,家庭是与私有制同步产生的,财产与权力主宰了婚姻。恩格斯以辛辣的语言批判,以财产与权力主宰的婚姻,实际上是“合法的强奸和卖淫”。至于近代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伊德”(id),意译为“本我”,所谓“文明”越进步,“本我”压抑得越严重。弗洛伊德原是精神病医生,以他长时期观察的结论,精神病的发病率几乎与性压抑的程度成正比例。这个问题,其实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提出过,庄子在他的书中以马来比喻人,野马在草原上奔跑,是最奔放的,把马系上笼头,钉上马掌,马的境况就难言了。这个问题怎样解决?难道要诅咒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回到远古时代去?这个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提出:在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发展中,如何更重视人性和人性的抒发?这个问题在中国不好提,因为实在“封建”得太长久了,就这个问题看《水浒传》,《水浒传》可以提供非常稀奇古怪而竟然习以为常的例证。但在中国的上古,情形并非这样,有这么一首诗:“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偶然相遇,就在野地里天真无邪地性爱,这几乎是中国古代的性解放。这首诗居然出自《诗经》的《郑风》。儒学的经典《五经》在中国遭遇两个极端,一方面被神圣化,捧上圣坛;一方面被妖魔化,贬下地狱。《五经》被看作“封建”,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竟然一点也不“封建”。让我们回到《诗经》的优秀传统。
记者:新妇女观的建立,往往以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前提,但事实上,现在很多女大学生,毕业后往往首先提到的是嫁一个好老公,讨论最热烈的是如何聪明地维护一个家庭的幸福,而绝少自己的理想、事业或其他追求幸福的道路,对此,你认为是妇女观的进步还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