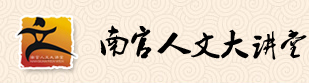山水诗——诗界里的一抹自然美
——访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何方形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庄向娟 王依乔 发布时间:2007年07月06日
记者:人类的本性是亲近自然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您觉得,关于这点,在山水诗中有没有体现?何方形:众所周知,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有地理、种族等多方面的因素,它是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生存环境中长期发展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洋溢着一种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中和”精神。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社会思潮的儒释道三教都为这一精神的奠定、完善和弘扬作出杰出的贡献。如《论语·侍坐》章通过孔子师徒的谈话,反映了儒家礼乐治国、先富后教的政治主张,其中曾皙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绘了理想中的生活情景,表达从大自然获得的一种身心解放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主体完全沉浸在对象之中,达到物我同一、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这一追求和谐的精神也反映到较为全面地展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山水诗中。如王维《汉江临泛》:“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以及《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阙题》“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等。又如李白的《望庐山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杜甫的《为农》:“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等。所以,歌德认为中国诗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
记者:孟浩然是山水诗的杰出代表。你能跟我们讲讲这位诗人以及他的山水诗的特色吗?
何方形:孟浩然早年隐居家乡鹿门山,后游长安应进士不第,遂东游吴越闽湘,以赏爱山水来作为情感落差的补偿。这样,人也就进入一片审美化的境界,获得前所未有的审美感受。孟诗就是这样的艺术结晶,多以“清”字自赏,超然独妙,气象清远。白居易《游襄阳怀孟浩然》“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旨在说明荆楚山水的毓秀灵气对他诗风的影响,其实,孟诗这一特色与诗人注重学习陶渊明清高绝俗的情趣和以白描手法创造清新浑融意境的艺术有密切关系,《李氏园卧疾》所谓“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以疏朗冲淡的笔意表现清幽的景物,自然超妙,恬淡深微。如《寻天台山》:“吾爱太乙子,餐霞卧赤城。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歇马凭云宿,扬帆截海行。高高翠微里,遥见石梁横。”当然,孟诗的风格也是多样的。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指出孟诗有一部分“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如著名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记者:山水诗是怎样产生与发展的,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自然环境及士人的精神世界之间有着怎样深层关系,其审美品格具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何方形:山水诗孕育于魏晋南北朝,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一时期,神州大地处于分裂状态,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经济动荡不安,甚至士人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佛老思想逐渐代替儒学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自然美也就在这一时期被唤醒并具有了真正的美学意义。有些人甚至选择山林作为人生最理想也是最后的归宿,也许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的一切悲苦与不幸,都将被自然的美与静所消解。
苍凉孤寂本就是生命的一种底色。无数骚人墨客常有仕途失意、心志不得伸展之痛,经历复杂的生命体验,但他们不是一味地咀嚼命运拨弄的苦涩,而是冷眼审视现实种种不平,然后大多自放于萧散之界,昔日的一腔壮志又往往转化为一片痴情,这样,他们就更会醉心于山水,徜徉在大自然的青山绿水之间,以审美观照者的眼光去审视人生,以期消融心中块垒,以平静的心来感应和品悟那自然生命的律动,找寻崭新的生命符号,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发现一种全新的人生境界。而一旦到了这样的境地,美的潜能就会充分地被释放出来,而这一潜能又唤醒艺术感受的天性,人们那种审美和爱美的普遍情感也得以被充分地激活,自然的某些美的属性和人们的审美心理、审美情趣也就进一步走向契合。于是,也就有了更多的用以展露审美主体观赏自然中获得一种审美解悟的艺术样式——山水诗,这大约就是苏轼《僧清顺新作垂云亭》“天怜诗人穷,乞与供诗本”的真正涵义吧。
山水诗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特深,喷涌着作者高尚、纯真的审美情感,但基本上没有越出儒、道、佛三家所划定的精神视阈。所以,山水诗既展现士人心中的高远之志、风雅之念,表达出他们的自得之乐、哲理之趣,一些作品也具备“方外”之味,正如赵抃《次韵范石道龙图三首》所说的:“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
记者:山水诗在古典诗歌中大放其彩,但现代诗歌其实已经走出了山水诗的藩篱,现代人有没有必要去发展山水诗,我们现在又应该以怎样一种审美心态去理解和欣赏山水诗。
何方形:山水诗在历史上确实大放异彩,实际上山水诗在现当代诗歌中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孔孚的山水诗等。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对这一切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发现、重新开掘。陈函辉对徐霞客说的“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永远是我们从事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枚《遣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是绝妙词”,就应该是我们现在理解、欣赏乃至创作山水诗的基本审美心态。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2006年出版了《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这一著作,那您能跟我们简单聊聊中国山水诗的审美艺术流变吗?
何方形:我国的山水诗作为一个演进着的生命之流,萌芽于先秦两汉,孕育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宋,明清后继续得以发展和深化。《中国山水诗审美艺术流变》一书200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人希望较为全面地考察中国山水诗的审美特质,梳理其艺术流变脉络,把握其多元化的复合美感这一精神内涵,尤其注重发展进程中审美艺术传承、流变与创新的精神实质。至于有没有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只有恭候社会的评判了。目前本人正承担2007年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浙江山水文学史》课题的研究工作,力争有新的成就报效社会。
最后要强调的是,以上所论多是一孔之见,不当之处,请各位多加教正!
记者:您太谦虚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