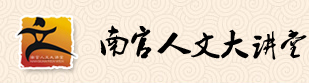我眼中的蒲华
——访嘉兴画院副院长、嘉兴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张文野
文章来源:路桥图书馆 作者:庄向娟 发布时间:2007年08月10日
记者:张院长,首先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来路桥开这次讲座。蒲华作品最让我迷恋的是他的竹画,他的竹画尤其有名,而郑板桥的竹画也非常人能及。相比较之下,您更偏爱谁画的竹?张文野:在我看来,蒲华的画竹比郑板桥的画竹更浑厚、大气、耐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相比之下,蒲华的竹显得有更多水分的滋润。在同样的秀挺风姿中,郑板桥画的竹略显单薄些,显得有骨无肉。按嘉湖土白的说法来讲是“单筋”,如按文人论画就叫做:“瘠”。
而蒲华的画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随着他自身审美观潜移默化的变易,虽然他写竹总体手法还是不变,但具体体现在对笔墨的感悟上,特别是用水一道,更是有了较大的发展。笔墨间水分含量的增加,会使画出的竹显得更浑厚、朴茂,也更令人感到生命活力的厚重。
记者:我们除了对蒲华所做的画赞赏不已、击节三叹之外,还知道,蒲华的书法也自成一派。您能给我们讲讲蒲华的书法成就吗?
张文野:蒲华的书法自称得笔法于吕岩(即吕洞宾)和白玉蟾(即葛长庚),但仔细考察一下,此两君的书法流传极其稀少,存世者可谓罕见,有如凤毛麟角,因而连王蘧常都不得不认为蒲作英大概是“玄妙其说,以自神其笔法罢了”。王蘧常的父亲王甲荣先生比蒲华大概小十多岁,曾与蒲华多有交往——大概是一种忘年交之类的友情吧。据他告诉王蘧常说的“蒲华学书入手仍是由二王,尤近于献之,后又爱东坡书,最喜用苏字笔意书陶潜诗句”云云。我认为王甲荣所述蒲华的这种笔致应该是属于蒲氏早年所为,根据现有蒲华较全面的书迹资料来看,似乎并不能仅仅满足这种说法。
在蒲华美术馆收藏了一副蒲华于“庚子(1900)重阳后七日”书写的上款为“逸庐主人”的长联,线条质量劲紧,结体与苏字大不相类,且用笔讲究,如锥画沙,近涩而得一留字诀,一反他中早期浸淫帖学的流美景象,倒更多的是有魏碑的意趣。这年蒲华已是69岁,应是已渐近老景,结体和用笔都能较稳定地体现他自己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由这副对联的笔意来分析蒲华晚年书法风貌的变易,倒是更契合乾嘉以来帖学式微而碑学兴起的时代大趋势。
记者:纵观蒲华的书法,世人最推崇的当数他的行草。我想,以您对蒲华的了解,肯定也相当了解蒲华的行草。
张文野:蒲华的行草是他书法中最有成就,因而也是更为世人所欣赏的。
当清中晚期时,行草书既有郑板桥、邓皖白等楷模在前,又有包安吴、沈寐叟、康有为等肆力近旁,先后辉映,皆卓然成家。但蒲老先生是概不相涉,丝毫不受影响。除了他自称得笔法于吕岩和白玉蝉外,论者每谓其笔法更有可能得自其幼时在寺庙的“扶乱”开沙盘时的那种“如锥划沙”的感觉。这种推测应该说不无道理,至少蒲华从这中间悟得了用笔的笔法还是有可能的。正如“草圣”张旭从公孙大娘舞剑器里悟得笔法是一样的道理。
记者:蒲华有幅年款为“丁丑春日”的竹石图轴属于他中壮年时期的作品,据推测,应是他客居台州时期所作。蒲华的这一段,对路桥的听众来说,颇具吸引力,您能跟我们讲讲这段吗?
张文野:蒲华作这副作品时,他虽正值壮年,但是在台州的生涯却实在不怎么样。做幕僚当然是端着别人的饭碗,自己艺术家的个性只能且先压一压再说,但是蒲华竟不太在意这俗世的规矩,也不顾太我行我素后将对饭碗有妨,仍是自说自话,结果饭碗丢了又找,找了又丢,弄得只能寄住寺庙,连衣食都有虞起来。他这时46岁,书画技艺已日趋成熟,所作书画作品颇得当地绅士认可,也为社会人士喜爱,因此虽不能像领俸禄般月月保证有固定进项,但糊口尚可,甚至时不时还会有点积余。
蒲老先生是性情中人,对阿堵物看得并不很重。蒲老先生一生没有女人给他当家,他对生活的料理是很欠缺的,卖画得来的钱就花掉,全然不顾明天怎么办。因此,许多时候往往把自己弄得很窘迫,给许多人留下的印象是连火仓都开不出来的穷酸相。这样说并不是空穴来风,大家知道蒲华是个文人画家,因此文人有的一些顽劣癖好他也一般都有,比如对于文玩古董的爱好等等。就说收藏文玩吧,那是很耗钱的雅事,蒲华虽然有时弄到四处蹭饭甚至要住庙的境地,但此时的他却已成为后来的海上“九琴十砚楼”置办了最早的两张古琴,这种东西即使是在清末那种社会急剧衰落的时期也不会太便宜的。因此,我想在蒲华买后来的七张琴和十块砚时说不定就会含有卖掉这幅墨竹的银子在内吧。
记者:蒲华与别的画家、书法家有所不同,他在艺术创作上是个勤于动笔的人。能否在这方面,告知读者几个故事?
张文野:蒲华是个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画到哪里,从不吝惜自己的笔墨。他既爱写爱画,也愿写愿画。别人酒肉银钱请他写画他就写画,有时别人并未请他动手,他也手痒痒只想动手写几下,画几下,甚至发展到只要看见有纸墨笔砚就拖过来又写又画,一直要弄到墨尽纸罄才肯罢手。
台州古老相传当时课学的塾童只要听说蒲华来了,就纷纷把纸张笔墨或作业本藏起来,以免被蒲华看见拿来写掉、画掉。当然这种传说可能有夸张失实之嫌,但至少蒲华对书画嗜僻之深、痴迷之狂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样的不看场合、地点都肯动手,都想动手,势必造成产品多而泛滥的局面,多而泛滥势必不可能件件精品。因此,蒲华的东西看多了,就会发现他精得极精,令人爱不释手,珍若拱壁;而粗疏之作却也不在少数,常常令人扼腕叹息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