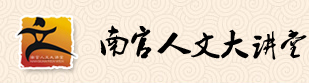潘天寿对发展民族艺术的宏观思考与实践
——访中国美院教授、潘天寿基金会副会长卢炘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庄向娟 发布时间:2008年02月22日
记者:二十世纪中国画领域纷争是颇为激烈的,而潘天寿是中流砥柱,对民族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卢教授,潘天寿作为中国画“特色论”的带头人,他的学术主张是什么?卢炘:潘天寿的学术主张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即:发展民族绘画,振兴民族精神,坚持民族特色,反对中西融合。他的学术主张具有鲜明性、针对性和一贯性。
记者:您能详细讲解下潘天寿的“四论”吗?
卢炘:“精神食粮论”要义:其一,认定文化艺术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其二,要创造美的情趣以养身心;其三,艺术当与旧文人的游戏把玩不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他不但一遍遍将艺术称之为精神食粮,而且对于艺术产品的生产者,又有一种合时代的自觉的新要求。
“民族精神结晶论”是潘天寿一生数十万字画论的最重要的基石。潘天寿为何一再强调民族风格、民族精神,原因很清楚,因为有人要“西化”,要取消中国画,他不能答应。他针对性很强,他要捍卫民族绘画。同时,请注意,在所有关于中国画的论述中,他从来不局限于就中国画谈中国画,着眼之处皆是整个文化领域,而分析种种文化现象又总是紧扣民族精神。
潘天寿字画论首先反复论证艺术与科学的不同,艺术是要讲究艺术主体与风格的。他以饮食爱好作比喻:统一是相对的,差别是绝对的,艺术也是一样。由此,得出“艺术不同论”。艺术与艺术要有不同,这包括两方面: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各民族的艺术不相同;就个别艺术家而言,要有个性,要独创。
在他那个时代,主张继承传统,借古开今,在传承中发展的中国画家并不少,但就个人成就和态度的坚定性而言,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当推潘天寿为最。他一遍遍告诫自己的同道和大批莘莘学子:对民族艺术一定要有自信。由此,得出“民族绘画自信论”。
分析潘天寿关于发展民族艺术的学术主张之立论基础,我们概括出以上四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十分严密的。 “民族绘画自信论”,除了要对民族绘画的历史成就有基本把握, “艺术不同论”才是其最本质、最重要之理论前提;“民族精神结晶论”则是对“精神食粮论”之深化,又是“民族绘画自信论”之最后归宿。
记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林风眠等人提出了“调和论”,潘天寿曾含蓄地反对过。后来,潘天寿形象地把中西绘画成就比喻为两大高峰,借以拉开距离以增加高度,这就是著名的“拉开距离说”。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学说吗?
卢炘: “拉开”和“调和”,实际即“分”和“合”。世事主合还是主分,大凡两者相比,大者强者主张合,因为合了以后他为主;小者弱者主张分,因为分了以后不至于被吃掉。大到国家地区是这样,小到企业公司、家庭也是如此。
我国的美术界从上世纪初开始,西风刮得比东风强,一会儿来自欧美,一会儿来自苏联。我们的美术教育几乎都是西式教育,有人会说现在的学校教育取自西方,西方先进嘛,学先进有什么错。问题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普通美术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只学素描、水彩,根本不学中国画,中国画已经被西画“化”掉了,至少五六十岁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近几年情况可能有改变。
问题很清楚,有了西方艺术的大量涌入,有了“融合”,有了调和论,在西画的吞并势头之下,潘天寿才提出要保持距离、要拉开距离,目的是保护自己民族的艺术。潘天寿要拉开距离,也就是使民族艺术的特色得到加强。另外,潘天寿提出与“调和”对立的“并存”主张,不存在否定西画的意思。至于如何拉开距离,潘天寿也说得很明白,这就要“扬长避短”。
记者:潘天寿还有个著名的“借古开今说”,对吧?
卢炘:没错。20世纪初期,西方新的美术思潮和流派的兴起,都是以“反传统”为口号的,甚至没有出过坚持传统模式的革新大师;与其相比,中国的“借古开今”口号似乎不够响亮、不够彻底,但中国画坛却实实在在出现了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样的革新大师。对于中国而言, “借古开今”没有丝毫保守的成分,却是一个进取的口号,口号本身其实也不是潘天寿的独创。只是潘天寿所处的时代——20世纪传统不受重视,重提此论, “借古”有某种校正之作用, “开今”又有“创新”之启示,所以颇有现实意义。
可以说潘天寿“借古开今说”,给中国画“扬长”指出了一个方向,需要再强调一下的是:借古,并非简单的临摹古人,古人重临摹也重写生;开今,必须有今人的情感、精神面貌融会其中。潘天寿反对“推翻一切旧东西,才能建立新东西”的观点。
潘天寿就艺术的“源与流”、 “常与变”、“共性与个性”都有过非常精辟的辩证论述。所以,著名美学家王朝闻称其“掌握了和运用着辩证法”、 “这个堪称中国文化的骄傲的大画家,同时也是一个出众的理论家”。
记者:作为一个艺术大师,在研究传统入手、抓紧教学改革的基础上,还应该推陈出新。那么,潘天寿在艺术创新上,有哪些表现?
卢炘:简单地说,表现在五个方面:改变传统折枝花卉的画法,把花鸟放到大自然中去表现;承文人画的优秀传统,改变文人画的图式,在构图方面有大的突破;尝试花鸟画与山水画相结合的新画作问世,大别于前人;推出巨帧大画,针对“中国画不能画大画”论给予有力反驳;创作指墨作品,发展中国画的特色。
记者:潘天寿在艺术创作上是收获丰硕的,这得益于什么?
卢炘:天、地、人三者皆备,是其创获的必然性。
从时代需要来讲,潘天寿自觉地担起了捍卫文人画的重任,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他终以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杰出成就,在三次大冲击中,成了中国画领域的中流砥柱。
从个人素养来讲,他事业至上,放眼全球,一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具有抓大事的领袖气质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潘天寿的独立人格向来被美术界所崇敬。他的人生态度是率真处世、务实求真。
从客观条件来讲,1957年美术界批了民族虚无主义,时任国立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潘天寿,正是在此时被推到了台前,从此他成了美术界执牛耳的人物,潘天寿得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空间;潘天寿同时兼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苏联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文革以前的那些年,国内政策有过相对宽松的一段时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也有过一些改变,老画家、老教授相对受到尊重,他们的意见也常常被领导采纳;潘天寿画了那么多创新的大画,自然也是客观上允许,有需求。
记者:潘天寿做为一名历史人物,他对社会有着怎样的意义?
卢炘:潘天寿真正的意义及影响在于他身后,民族艺术的发展没有停止,他的理论与实践,促成了“三个形成”:即,形成思想体系、形成教学体系、形成一个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