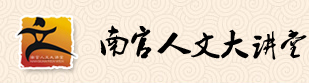庄子与武侠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李承静 发布时间:2016年07月01日
□本报记者 李承静记者:熟悉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读者或许对这段对话并不陌生。
霍青桐忽问:“那篇《庄子》说些甚么?”陈家洛道:“说一个屠夫杀牛的本事很好,他肩和手的伸缩,脚与膝的进退,刀割的声音,无不因便施巧,合于音乐节拍,举动就如跳舞一般。”香香公主拍手笑道:“那一定很好看。”霍青桐道:“临敌杀人也能这样就好啦。”陈家洛一听,顿时呆了。《庄子》这部书他烂熟于胸,想到时已丝毫不觉新鲜,这时忽被一个从未读过此书的人一提,真所谓茅塞顿开。
这段对“庖丁解牛”的全新解读让很多人纷纷感慨:原来庄子可以这么读!其实,庄子与武侠的渊源远不止《书剑恩仇录》一部小说,金庸的《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里就有或多或少的描写,就连现今很多武侠电影也都纷纷折回头去,从庄子和他的作品里面“挖宝”。张教授,您是如何看待武侠作品的“庄化”现象呢?
张亦辉:实际上,庄子本人的形象,就极易让人想起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造诣至深,功夫盖世,出离尘埃,独孤求败,无用乃至用,无招胜有招,逍遥于山林,相忘于江湖。毫不夸张地说,庄子就是最早最酷的那个世外高手。而《杂篇·说剑》这样的文章差不多可以看成是中国的第一篇武侠小说。
记者:那么,庄子作品里都有哪些相关的细节描写,让后世的武侠作品创作者们兴致勃勃地去“淘宝”呢?
张亦辉:在我看来,《庄子》与武侠之间,既有形似又有神似。一部《庄子》其实是中国武侠小说与电影的丰沛源头,庄子的道家思想、生命境界、艺术想象与一剑封喉般的超拔文风,对后世武侠的启发与影响可谓普遍而深远。
就说金庸吧,他的武学体系就明显受益于庄子。在金庸小说中,豪客侠士均有庄学气质,他们对武功的追求便是对境界的追求,非精神境界高者不能达到武功的臻美至境,凡达到武学至高境界者又必有精神上的大境界。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剑魔独孤求败练剑的四重境界(何尝不是人生的四重境界)和张无忌练太极剑全然忘怀反而能出神入化两例。而这种大境界总是无形无象无物无己的,恰如庄学的生命境界。
金庸的代表作《天龙八部》中就有一个“逍遥派”,其独门武功是“北冥神功”。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在玉山参详前人所遗的武学奇典,居然是一部《庄子》,其武功绝招直接受“庖丁解牛”的启迪而练成。
庄子的《庖丁解牛》先从总体上描画了庖丁解牛的熟练、利索与舞蹈般的节奏感,庄子用音乐来比拟庖丁解牛的神妙状态(“莫不中音”)。后世武侠也沿袭了这一方式,用音乐来比拟或表现武功。张艺谋的电影《英雄》棋院打斗那场戏,无名与长空甫一接招,那个弹古琴的老先生要起身离开,无名便在打斗间隙,让那个老先生“再抚一曲”,并在那个碗里扔了几个先秦刀币。接下来,琴声响起,两个高手树一样屹立在那儿,我们听到无名的旁白“武功琴韵虽不相同,但原理相通,都讲究大音稀声之境界”,便是这个道理。
我认为,庄子的天才之处在于,他的叙述总能从现实的日常行为和情景出发,通过精准的细节刻画,借助超拔极致的想象,利用匪夷所思的创造性的诗学语言与修辞(如通感),从形而下升华至形而上,从物质跃向精神,从具象上升到抽象,从现实转向魔幻,从技术演化到艺术,然后把艺术推向极境,推向自由之境,最后推向道极,这恰好是庄子所说的“道也,进乎技矣”。
这样的神笔妙文,才足以道出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