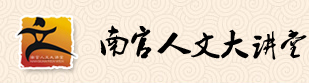从诺贝尔文学奖说开去——解读莫言
文章来源:今日路桥 作者:李承静 发布时间:2016年07月08日
□本报记者 李承静记者:2012年10月11日,对中国当代文学界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作家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结束了“诺奖无中国作家上榜”的历史,也让莫言个人的声望达到顶峰。莫言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作家?他的作品为何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顶级殊荣?
王慧:尽管过去了四年,但关于莫言,最热门的词汇依然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它的余温还能持续一段时间。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对莫言的评价极为中肯:“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他很好地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对于莫言的获奖,国内评论在一片弹冠相庆的背后,也有几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这是魔幻写实激发西方想象因而获奖的,也有人认为这是诺奖评委为了攀附中国文学市场而给的“人情奖”。对于种种不同的声音,莫言的态度倒是非常淡定,他表示:“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记者:有人说,莫言是一个很典型的地域特色的作家,他的人生经历便是他创作的宝库,对此,您怎么看?
王慧: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已经是国内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除了赢得一大批的读者之外,也给他带来很高的荣誉。其中,《红高粱》获得1987年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生死疲劳》获得2008年第二届红楼梦奖,《蛙》也曾获得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
莫言,这名来自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故乡高密东北方向的大栏乡更是被莫言拿来当作原型,构建出“高密东北乡”,这是一个充满近乎乌托邦式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用过去的美好,反衬当下的丑恶,用理想中的纯真,来渲染现世的浮夸。
记者:对高密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来自《红高粱》里的那一段:“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作为读者非常熟悉的一部小说,《红高粱》在莫言的一众著作里面享有很高的地位。王老师,您怎么评价这部小说呢?
王慧:《红高粱》以抗日战争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故事中塑造的一系列抗日英雄却都是正义和邪恶的化身。主人公余占鳌是一个热血汉子,身体里面充满了正义与野蛮,为了心爱的女人去杀人放火,并且霸占了之后成为他妻子的戴凤莲。余占鳌为报仇雪耻,苦练枪法,把曾经非礼过他妻子的土匪一网打尽。余占鳌抗日,但他并没真正地认识到抗战的本质。他身上散发着十分鲜活的人性,也充满了野蛮与无知的兽性。
在小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伦理道德边缘的红高粱世界,一种土匪式英雄,他们做尽坏事但也报效国家,他们缱绻相爱、英勇搏杀,充满着既离经叛道又拥有无限生气的时代气息。
在我看来,《红高粱》传递了一种自由、感性的生命精神以及自在、理想的生存状态。它不仅仅包含了丑和恶的东西,也包孕了美丑对立、善恶交织、瑕瑜互见的一种文化形态和审美形态。用鲍列夫的话说便是:文学应向现实和未来同时开放。